目录
快速导航-

关注 | 红绿灯
关注 | 红绿灯
-
关注 | 小说短巧,像一声叹息
关注 | 小说短巧,像一声叹息
-
中篇小说 | 卡农,或在昆明某处
中篇小说 | 卡农,或在昆明某处
-
中篇小说 | 过去进行曲
中篇小说 | 过去进行曲
-
短篇小说 | 洛浦公园一切顺利
短篇小说 | 洛浦公园一切顺利
-
短篇小说 | 白鬃狼的哭泣
短篇小说 | 白鬃狼的哭泣
-
短篇小说 | 瓯 柑
短篇小说 | 瓯 柑
-
短篇小说 | 蜜 獾
短篇小说 | 蜜 獾
-
短篇小说 | 孙大午的手术
短篇小说 | 孙大午的手术
-
散文 | 挖河记忆
散文 | 挖河记忆
-
散文 | 触摸乡愁
散文 | 触摸乡愁
-
散文 | 沿着河水漫步
散文 | 沿着河水漫步
-
散文 | 当一个作家支起画架
散文 | 当一个作家支起画架
-
散文 | 光明隧道
散文 | 光明隧道
-
散文 | 白水河
散文 | 白水河
-

青年计划 | 虫鱼鸟兽
青年计划 | 虫鱼鸟兽
-
青年计划 | 再见黄泉
青年计划 | 再见黄泉
-
青年计划 | 观念之于小说
青年计划 | 观念之于小说
-
细读 | 那一瞬的人性之光,不旁观,不凝视
细读 | 那一瞬的人性之光,不旁观,不凝视
-
笔谈 | 不顺的人生该如何严肃地表达
笔谈 | 不顺的人生该如何严肃地表达
-
笔谈 | 徘徊于城乡间的生命书写
笔谈 | 徘徊于城乡间的生命书写
-
笔谈 | 从趋城到逆城:小镇青年的价值重寻与人生转向
笔谈 | 从趋城到逆城:小镇青年的价值重寻与人生转向
-

回眸 | 记忆萦回,有关那山那人那狗
回眸 | 记忆萦回,有关那山那人那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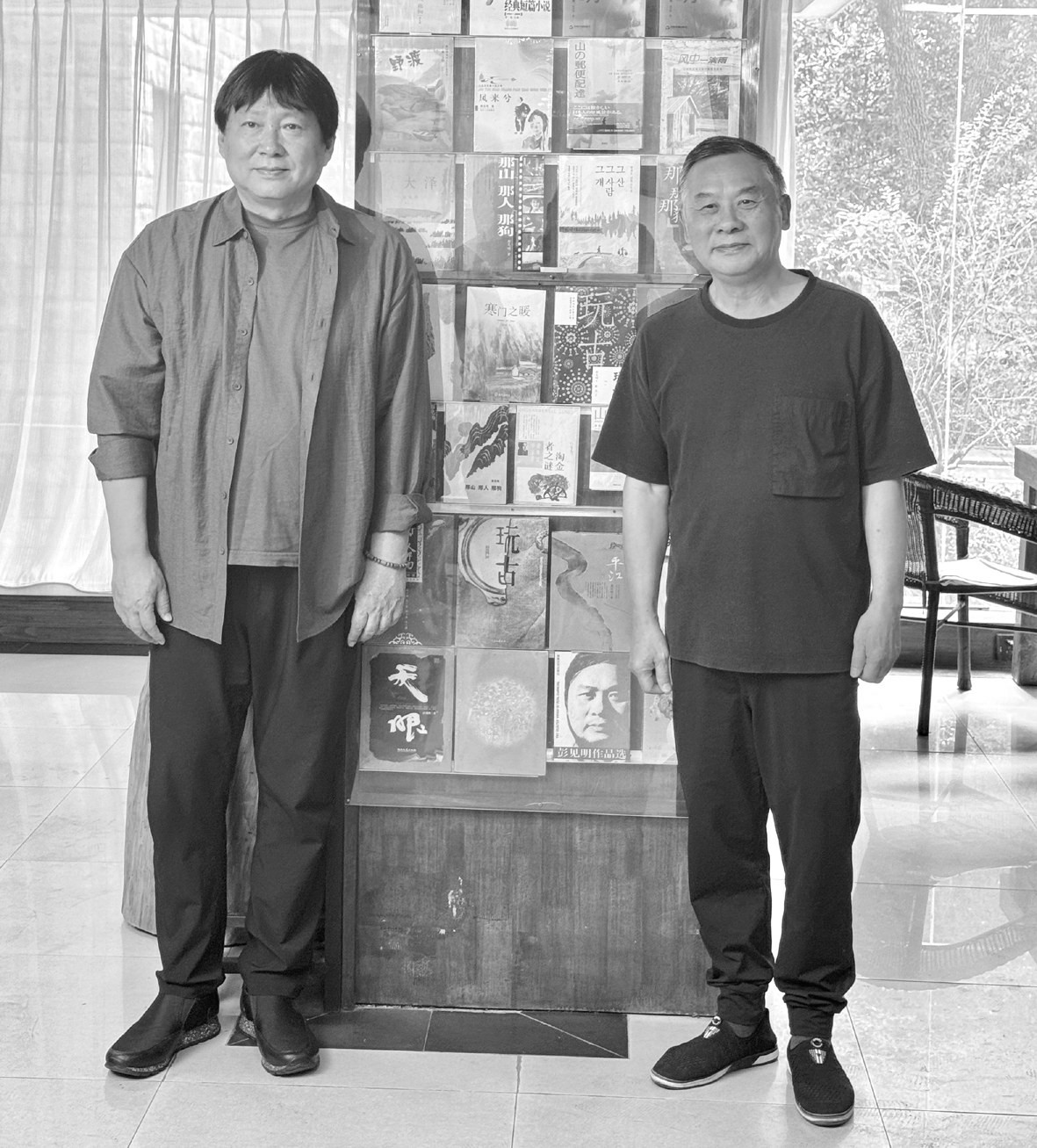
回眸 | 那小说 那电影
回眸 | 那小说 那电影
-

回眸 | 我们从湘北走来
回眸 | 我们从湘北走来
-
诗界 | 手模、哑剧与万花筒
诗界 | 手模、哑剧与万花筒
-
诗界 | 情境万花筒与穿透日常的耦合
诗界 | 情境万花筒与穿透日常的耦合
-
诗界 | 延时的鸟鸣
诗界 | 延时的鸟鸣
-
诗界 | 短歌行
诗界 | 短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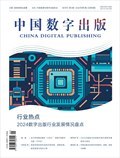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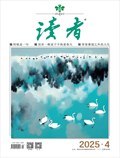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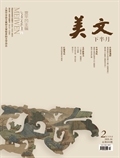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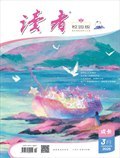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