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分类/
- 生活艺术/
- 视野
 扫码免费借阅
扫码免费借阅
目录
快速导航-

导读 | 导读
导读 | 导读
-

视点 | 这本书,让光绪下定决心变法
视点 | 这本书,让光绪下定决心变法
-

视点 | 维新变法始末
视点 | 维新变法始末
-

视点 | 戊戌政变的回忆
视点 | 戊戌政变的回忆
-

视点 | 谭嗣同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视点 | 谭嗣同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

视点 | 戊戌政变后,慈禧开始变法
视点 | 戊戌政变后,慈禧开始变法
-

大学之大 | 一个冷门专业的修行之路
大学之大 | 一个冷门专业的修行之路
-

大学之大 | 他们要数清中国的树
大学之大 | 他们要数清中国的树
-

大学之大 | 还不起学贷,美国年轻人跑路
大学之大 | 还不起学贷,美国年轻人跑路
-

美育 | 暮色自远而至
美育 | 暮色自远而至
-

美育 | 海棠依旧
美育 | 海棠依旧
-

美育 | 携一本书行走
美育 | 携一本书行走
-

美育 | 战国匈奴王冠
美育 | 战国匈奴王冠
-

美育 | 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人形器
美育 | 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人形器
-

美育 | 南宋·松间山禽图
美育 | 南宋·松间山禽图
-

美育 | 人为什么接受教育
美育 | 人为什么接受教育
-

美育 | 挽留时间
美育 | 挽留时间
-
美育 | 一枝自然之花
美育 | 一枝自然之花
-

美育 | 逆光
美育 | 逆光
-
美育 | 海岸线悖论
美育 | 海岸线悖论
-
美育 | 北窗浴绿
美育 | 北窗浴绿
-
美育 | 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
美育 | 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
-
美育 | 味觉的故事
美育 | 味觉的故事
-
美育 | 幸福时刻
美育 | 幸福时刻
-

生涯 | 我二十一岁那年
生涯 | 我二十一岁那年
-

生涯 | 当列宾遇见托尔斯泰
生涯 | 当列宾遇见托尔斯泰
-

生涯 | 困境中的莫奈
生涯 | 困境中的莫奈
-

通识 | 今天的食物为什么没有从前好吃
通识 | 今天的食物为什么没有从前好吃
-

通识 | 复杂的鸟鸣
通识 | 复杂的鸟鸣
-

通识 | 郑和的船队为什么没有绕过好望角
通识 | 郑和的船队为什么没有绕过好望角
-

教与学 | 我的儿子跟学校“八字不合”
教与学 | 我的儿子跟学校“八字不合”
-

教与学 | 在语文课本里读懂人生
教与学 | 在语文课本里读懂人生
-

教与学 | 阅读时,不要放过你的耳朵
教与学 | 阅读时,不要放过你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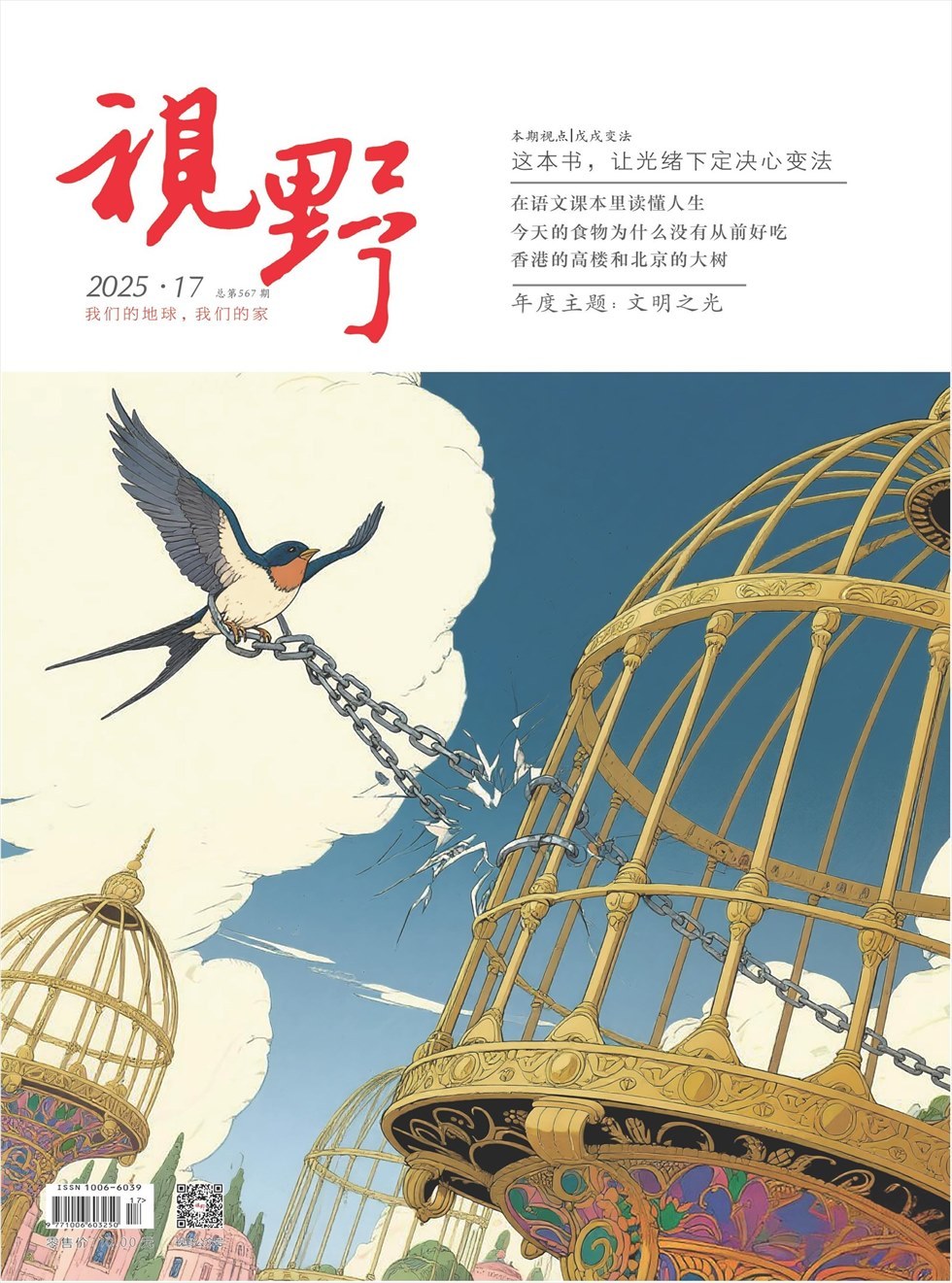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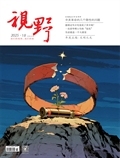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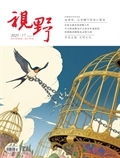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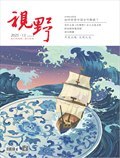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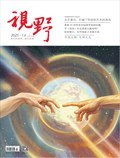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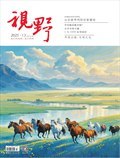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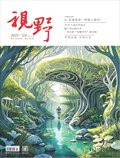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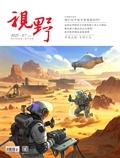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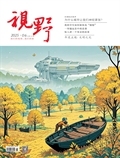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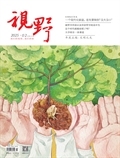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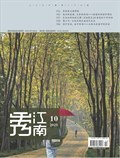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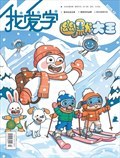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