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最美中国 | 灯的光芒(组章)
最美中国 | 灯的光芒(组章)
钢铁意志 一个用骨头点灯的人,绕过荆棘,跨过沟壑,越过山冈 卸下满身的暗,用黎明,紧紧地握住钢铁 你以执着、自信、决绝的目光,撑过了风雨 一个人的内心亮起来,钢铁也亮起来,一座钢城也跟着 亮起来 让钢铁亮起来,靠的是人的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 钢铁意志,是你一生的深度 凝聚光芒 血中有铁,需要的是爱;骨头里有钢,需要的是忠诚 一名普通职工把以厂为家深深地刻在灵魂里 需要的是自身的
-
最美中国 | 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散记(组章)
最美中国 | 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散记(组章)
陶家河 大部队北上长征去了,只留下伤员和一群送信的孩子。 伤员四散于闵家畈村,桦树沟村,塔耳岗村,陶河村,英太寨村等等,像种植于大别山的原上草。 为了保护伤员的藏身之地,送信的孩子躲过糖衣炮弹,又经受住严刑拷打。在陶河中学后山的庄稼地里,送信的孩子宁愿被埋进土里两米,也没把伤员从嘴里吐出来半点。 一块篮球大的石头成了历史的在场者。送信的孩子用头击石,最终也成为一块石头,沉默,坚硬,死守心中
-
最美中国 | 怒 江
最美中国 | 怒 江
大河,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使命,例如怒江。 无论高山峡谷,无论寂静与热闹,只要它经过,所有的时间与空间,仿佛全被打乱,然后,又继续发生。 河水奔流,不停地制造“惊”与“险”奇迹,不断创造一条大河的独特历史。 怒江。一如勇往直前的勇士,上到掀开层层白云的帘子,下到闯开一道道大山的门扉,在生命的道路上,跌宕起伏,哪怕被称为“潞江”或“那曲河”。照样奔驰不羁,因为生发于唐古拉山,它深谙青藏高原的内部
-
最美中国 | 在璀璨的大地上(五章)
最美中国 | 在璀璨的大地上(五章)
西狭颂 石头固守坚硬的秉性,山岩的面目遍及冷峻,这是神情的另一种表达,有风雨深凿浅刻的印痕。 河水是温柔的替身,低吟浅唱里藏着几分羞涩,每与石头狭路相逢,被撞碎的部分,会开出人世间最纯美的花。 挺拔的树木,灵魂从来没有屈服,一些枝柯已经丢盔弃甲,另一些还把碧绿披在身上,像山盟海誓保守着忠贞从终的执念。 零星的雪花适时落下来,把大地上所有的寒凉吻出充裕的感动,真诚盈胸,却不轻易说破。 凤凰
-
最美中国 | 上海叙事(组章)
最美中国 | 上海叙事(组章)
题记:醒来,是开在玫瑰上的玫瑰 是在翅膀上歌唱 是装满大海的大海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葡萄牙] 童家桥 如果我轻唤你的名字,你是否会以岩灰色的新尘和我确认眼神?如果我转身,轻拂你冰凉的额头,你是否,会以远古的纹路撑起我灼热的指尖与我相认? 童家桥,这座暗藏怯弱的古旧小桥,这支不敢按照原有秩序发声的被遗弃的旧曲,这烙刻在童年深处的名字,这一经读出就不禁使人颤动的三个字,此刻在三
-
星发现 | 西北物器(组章)
星发现 | 西北物器(组章)
水 缸 雨,从夜里落下来。 静静地,她们把岁月的伤痕渐渐抚平,裹紧身体的旧被子,像一块纱布,把土炕上的身影,勒成两道刺眼的闪电。 只有滴滴答答的水声,浇灌着苍老的睡梦。在秋天的夜里,她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幼年时代,梦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卷心菜在雨里收集潮湿的心事;小野菊在微风中摇曳,把伏下的身姿,重新拾起;孩子们头顶着编织袋做成的斗笠,越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去很远的村子上学。那时候,她们有着黝黑的头
-
星发现 | 晓寒云雾连穷屿(组章)
星发现 | 晓寒云雾连穷屿(组章)
潮落夜江斜月里 饮酒时,我想起唐朝的诗人。夜阑人静,清风不语,诗里的平仄依靠醇酿,我们一醉方休。潮起潮落的金陵渡口,乡愁是这样被困在夜里,涟漪撑不过江面,落入更加巨大的沉默。 醉酒并非醉得酒精的度数,夜里的思念,被江面与天空的斜度,夹在一条更为细长的缝隙里,始终安放不下太多深沉的词语,所以举杯,所以一仰脖就是一条江河。 秦楼楚馆今犹在,落花依旧入水流,断肠的江南,处处都有生情的景色,古镇的街
-
星发现 | 庭院里有风的薄衣(五章)
星发现 | 庭院里有风的薄衣(五章)
在庭院的上午 山的脊背在放松—— 阳光顺势,摘下了林中的雾气,转眼间,上午如镜子般明亮。木质的旧桌椅,看护着庭院的领地。 我在门前落座,细细欣赏天空中,几团擦拭过灰雾的白色餐巾。 小窗口被光线堵住了嘴巴,门前的风声蠢蠢欲动,想要去招惹远处的森林。 桌面上,杯子从我的右手边起身——水的心脏悬停空中,口渴发生了,但并不是迫切的渴意。 流淌的声音走动起来,走向喉咙的无人之境。我的目光捕捉了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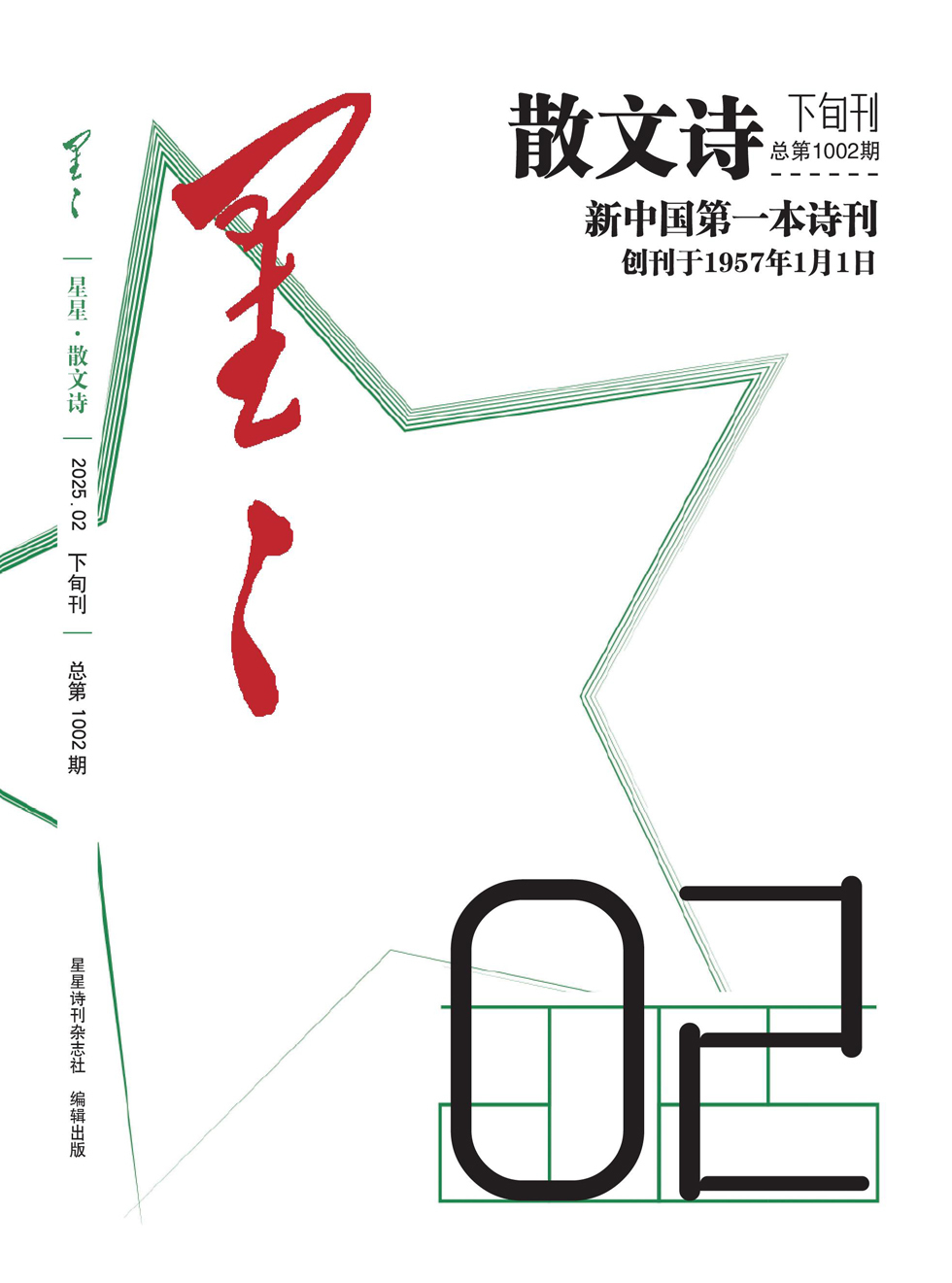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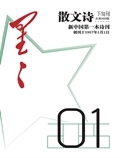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