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开卷有益 | 不要把你的菜强加给别人
开卷有益 | 不要把你的菜强加给别人
不久前,我在饭店组织了一场亲友聚餐。最后一道汤菜是西湖牛肉羹,我尝了一口,简直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西湖牛肉羹。于是,我起身给每个人盛了一小碗西湖牛肉羹。 我本以为我的热情会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都会对这道汤菜赞不绝口。谁知,有的客人抿了一小口就放下碗了,有的甚至连尝都没尝。他们客气地推辞着:“饭吃得太饱了,汤喝不下了。”“我不吃牛肉,牛肉羹也不吃。”“味道还不错,不过我习惯饭后吃点
-
特别推荐 | 天工
特别推荐 | 天工
一个伟大的“奇想”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能记得当年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有的人也许会说:“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震惊了世界!”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说起,这年的7月,上海市举办了一场规模颇大的科技展览会,名曰“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开展这天,偌大的展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模型,墙壁上也挂满了人们已经付诸行动和尚未付诸行动的宏伟科技蓝图。一行人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展厅
-
精品 | 高手一句话
精品 | 高手一句话
津门胜地,能人如林,此间出了两位卖茶汤的高手,把这种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卖得远近闻名。这二位,一位胖黑敦厚,名叫杨七;一位细白精明,人称杨八。杨七杨八,好赛哥儿俩,其实无亲无故,不过他们俩的爹都姓杨罢了。杨八本名杨巴,由于“巴”与“八”音同,杨巴的年岁长相又比杨七小,人们便错把他当成杨七的兄弟。 不过要说他们俩的配合,好比左右手,又非亲兄弟可比。杨七手艺高,只管闷头制作;杨巴口才好,专管外场照应
-
精品 | 熬鹰
精品 | 熬鹰
他直勾勾地盯着鹰的眼睛。 鹰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晴。 他和鹰之间,距离不过一丈。狭小的屋子里,人鹰对视,时间仿佛静止。 人眼如刀,鹰眼似剑。这场无声无息的较量,被称作“熬鹰”。 人和鹰,已经熬了八天。 地上有两根木桩,木桩之间连着一条粗粗的麻绳,麻绳中间是一个纺锤形的绳团,鹰的两只利爪牢牢抓着绳团。鹰立在鹰架上,往日雄风已隐去许多。但它的眼神依然犀利。 他坐在鹰的对面。 他的眼里只有鹰
-
精品 | 碎嘴
精品 | 碎嘴
老街小吃“三件宝”,酥烧薄粉烫面饺。 吃酥烧,老街人习惯到常松家,他家那个“常记”酥烧,表皮金黄,做馅儿的葱是常松家人一根根挑的,不仅馅儿和面的比例恰到好处,馅儿里的葱白和葱叶也比例适中,葱香味儿浓,咬起来酥脆,吃到嘴里发黏。吃薄粉,要数启亮家,薄粉主料是豆粉,乍看像本地人喝的糊糊,却比糊糊亮,又像是南方人喝的浓粥,但比浓粥稠。盛薄粉的碗也有讲究,要用亮堂一点儿的碗,不用黑碗。薄粉在碗里,静看像
-
精品 | 英雄
精品 | 英雄
年初,上级安排我整理一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教材,查资料时我发现一个叫樊海堂的人,晋察冀时期的游击大队长,是个战斗英雄。他几次因犯错误被处理,后来又被平反。从大的方面说,他绝对算英模人物,只是能不能编进教材,我一时拿不准,就把他的资料选放到一边,所以印象深刻。 我找过曾在晋察冀打鬼子的军分区老首长了解樊海堂的情况,他说:“他是响当当的人物,打了很多次胜仗,是个英雄。军区抗敌剧社还演过他的事迹。”
-
精品 | 擞儿
精品 | 擞儿
这几天,C一个劲儿地往村民文化广场跑。作为初学乍练的京剧票友,他在广场票房拜了刚从城里回来的村民W为师学戏。W是城里票房小有名气的琴师,据说他是卖掉城里楼房回来的。老人家因何告老还乡?是怀土之情,还是叶落归根?抑或是……不得而知。反正只是跟他学戏而已,C不愿为与己无关的事费心思。 W第一次在老家收徒,就遇上了悟性极高的村民C。每每看到爱徒有板有眼地演唱,W虽不喜形于色,却也十分卖力地拉京胡伴奏,
-
精品 | 放蜂人与火车
精品 | 放蜂人与火车
在我家的后山上,有数不胜数的树。有了树,就有了花,连翘花、槐花、野桃花、杏花、杜鹃花,争着抢着开。春天来的时候,花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开了。在花开之前,放蜂人就来了。 放蜂人是老石。 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办法把那一箱箱蜜蜂运来的,等我看到时,那些蜂箱已经在村外的林子里摆着了。他的蜜蜂整天绕着村子嗡嗡嗡地飞。 老石搭一顶绿帆布的帐篷,里面有锅碗瓢盆、一只小小的煤油炉子和一张地铺。菜是不用带的,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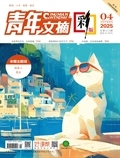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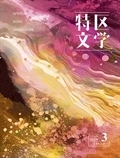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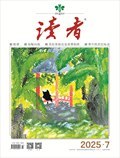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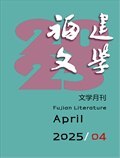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