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卷首语 | 致敬播种的人
卷首语 | 致敬播种的人
-

话题 | 长期主义是跳出内卷的最好选择
话题 | 长期主义是跳出内卷的最好选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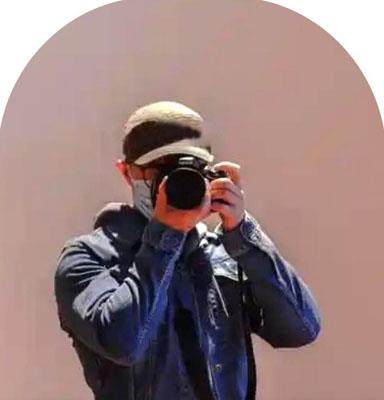
话题 | 普通人就别想当自媒体博主了
话题 | 普通人就别想当自媒体博主了
-

世相 | 我们的裁缝店
世相 | 我们的裁缝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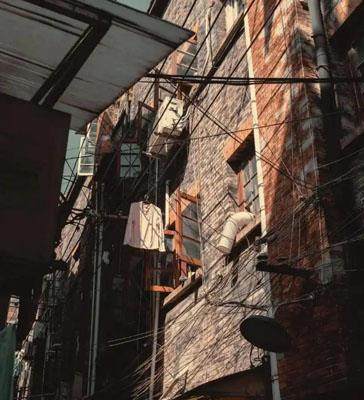
世相 | 关于“老破小”的回忆
世相 | 关于“老破小”的回忆
-

人物 | 蔡磊: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人物 | 蔡磊: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

人物 | 天才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物 | 天才究竟是什么样的
-
文明 | 古装的拖尾那么长,蹭脏了怎么办
文明 | 古装的拖尾那么长,蹭脏了怎么办
-

文明 | 烟雨故宫
文明 | 烟雨故宫
-

文明 | 人类为什么要探索太空
文明 | 人类为什么要探索太空
-
文明 | 密码传奇
文明 | 密码传奇
-

悦读 | 姥姥的教育方式
悦读 | 姥姥的教育方式
-
悦读 | 胆小的乘客
悦读 | 胆小的乘客
-
悦读 | 舀蝌蚪
悦读 | 舀蝌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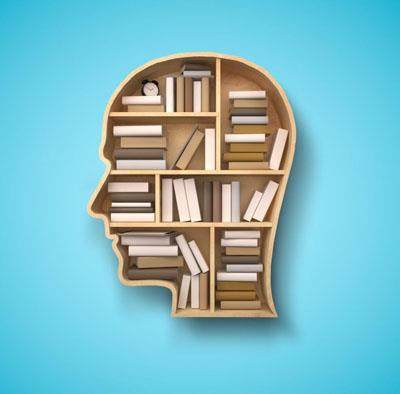
悦读 | 纸质的时间
悦读 | 纸质的时间
-

悦读 | 冬夜失眠症
悦读 | 冬夜失眠症
-
悦读 | 肥瘦之间
悦读 | 肥瘦之间
-
生活 | 不要把你的菜强加给别人
生活 | 不要把你的菜强加给别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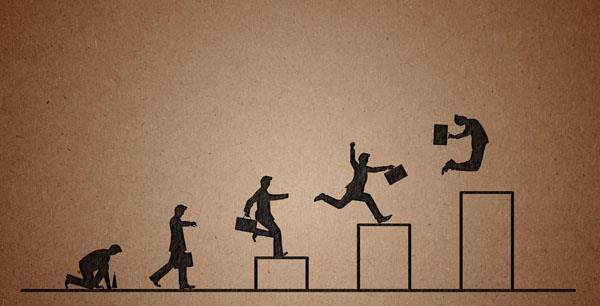
生活 | 阅读的舒适区
生活 | 阅读的舒适区
-

生活 | 没有边界的亲密
生活 | 没有边界的亲密
-

生活 | 不为小事消耗
生活 | 不为小事消耗
-
生活 | 漂亮也是一种天赋
生活 | 漂亮也是一种天赋
-
荐书 | 打破羞耻枷锁
荐书 | 打破羞耻枷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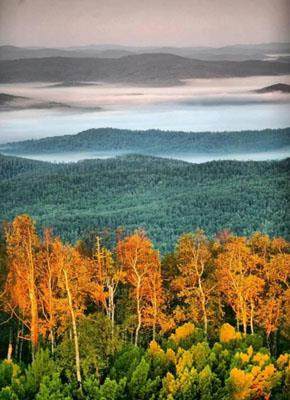
荐书 | 大兴安岭的学生
荐书 | 大兴安岭的学生
-
荐书 | 天才编辑与海明威
荐书 | 天才编辑与海明威
-

荐书 | 参观王室图书馆
荐书 | 参观王室图书馆
-

荐书 | 老而孤独,你惧怕吗
荐书 | 老而孤独,你惧怕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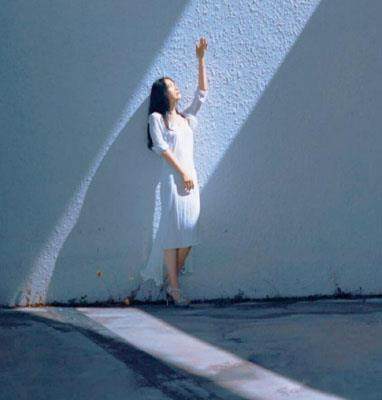
智识 | 坏情绪让血管很受伤
智识 | 坏情绪让血管很受伤
-
智识 | 如何用一枚曲别针换一辆车
智识 | 如何用一枚曲别针换一辆车
-
智识 | 神奇的“4%法则”
智识 | 神奇的“4%法则”
-

智识 | 用户需要改变吗
智识 | 用户需要改变吗
-
博览 | 从来不存钱的巴西人
博览 | 从来不存钱的巴西人
-

博览 | 域外理发记
博览 | 域外理发记
-
博览 | 禁养35年后,新加坡决定对猫高抬贵手
博览 | 禁养35年后,新加坡决定对猫高抬贵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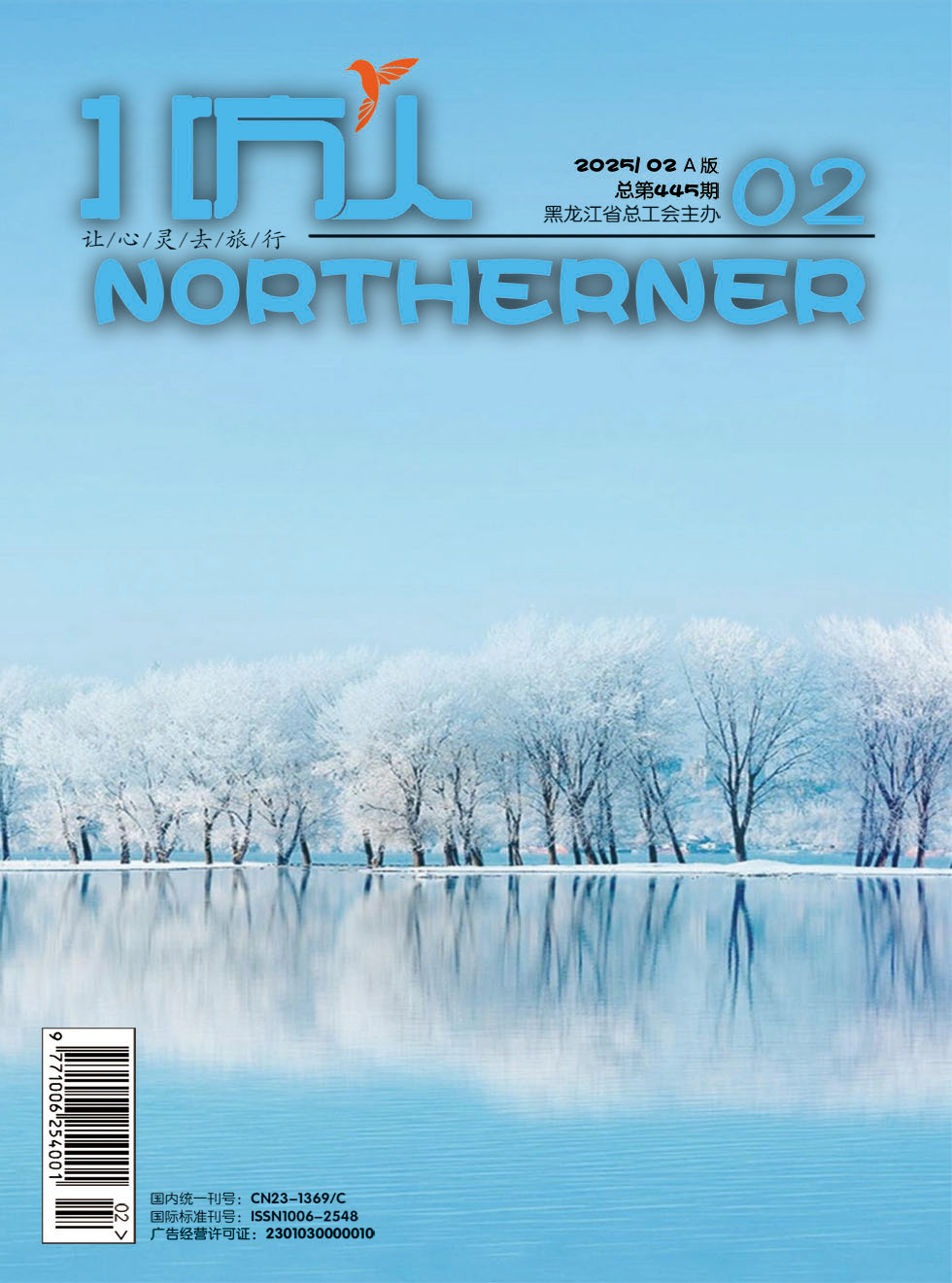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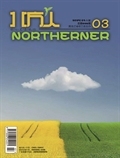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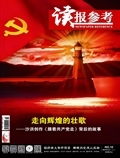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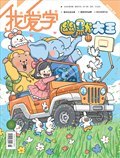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