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新时代诗观察 | 诗歌,本是大众的事业
新时代诗观察 | 诗歌,本是大众的事业
-
新时代诗观察 | 对诗的再次发明
新时代诗观察 | 对诗的再次发明
-
新时代诗观察 | 上小红书,做个诗歌博主
新时代诗观察 | 上小红书,做个诗歌博主
-
新时代诗观察 | 我们为什么不读诗
新时代诗观察 | 我们为什么不读诗
-
诗家对谈 | 诗评家应该有“第三只眼”
诗家对谈 | 诗评家应该有“第三只眼”
-
诺奖诗人诗作评鉴:谢默斯·希尼 | 穿透生命之根
诺奖诗人诗作评鉴:谢默斯·希尼 | 穿透生命之根
-
新诗集快评 | 乡土诗歌抒写:传统、时代变奏与前景
新诗集快评 | 乡土诗歌抒写:传统、时代变奏与前景
-
新诗集快评 | 向内的视界,向外的通途
新诗集快评 | 向内的视界,向外的通途
-
新诗集快评 | 古典与当代:在修辞中互构的汉语诗歌传统
新诗集快评 | 古典与当代:在修辞中互构的汉语诗歌传统
-
编辑读诗 | 《需要》《雪》《初恋》
编辑读诗 | 《需要》《雪》《初恋》
-
编辑读诗 | 《大雪》《冬晨》《多好的日子》
编辑读诗 | 《大雪》《冬晨》《多好的日子》
-
如何写好一首诗 | 《无名石》诞生背后的成因
如何写好一首诗 | 《无名石》诞生背后的成因
-
如何写好一首诗 | 和一首诗歌的相遇
如何写好一首诗 | 和一首诗歌的相遇
-
诗歌地理 | 一半,一半(外二首)
诗歌地理 | 一半,一半(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在余东竹编馆(外二首)
诗歌地理 | 在余东竹编馆(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烂柯山之读(外二首)
诗歌地理 | 烂柯山之读(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江郎山(外一首)
诗歌地理 | 江郎山(外一首)
-
诗歌地理 | 寄衢州(外二首)
诗歌地理 | 寄衢州(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樵隐岩(外二首)
诗歌地理 | 樵隐岩(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下淤帖(外二首)
诗歌地理 | 下淤帖(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严村埠头小坐(外二首)
诗歌地理 | 严村埠头小坐(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江郎山(外一首)(1)
诗歌地理 | 江郎山(外一首)(1)
-
诗歌地理 | 偶遇北门老街(外二首)
诗歌地理 | 偶遇北门老街(外二首)
-
诗歌地理 | 乡土诗歌的美学探索与多元面向
诗歌地理 | 乡土诗歌的美学探索与多元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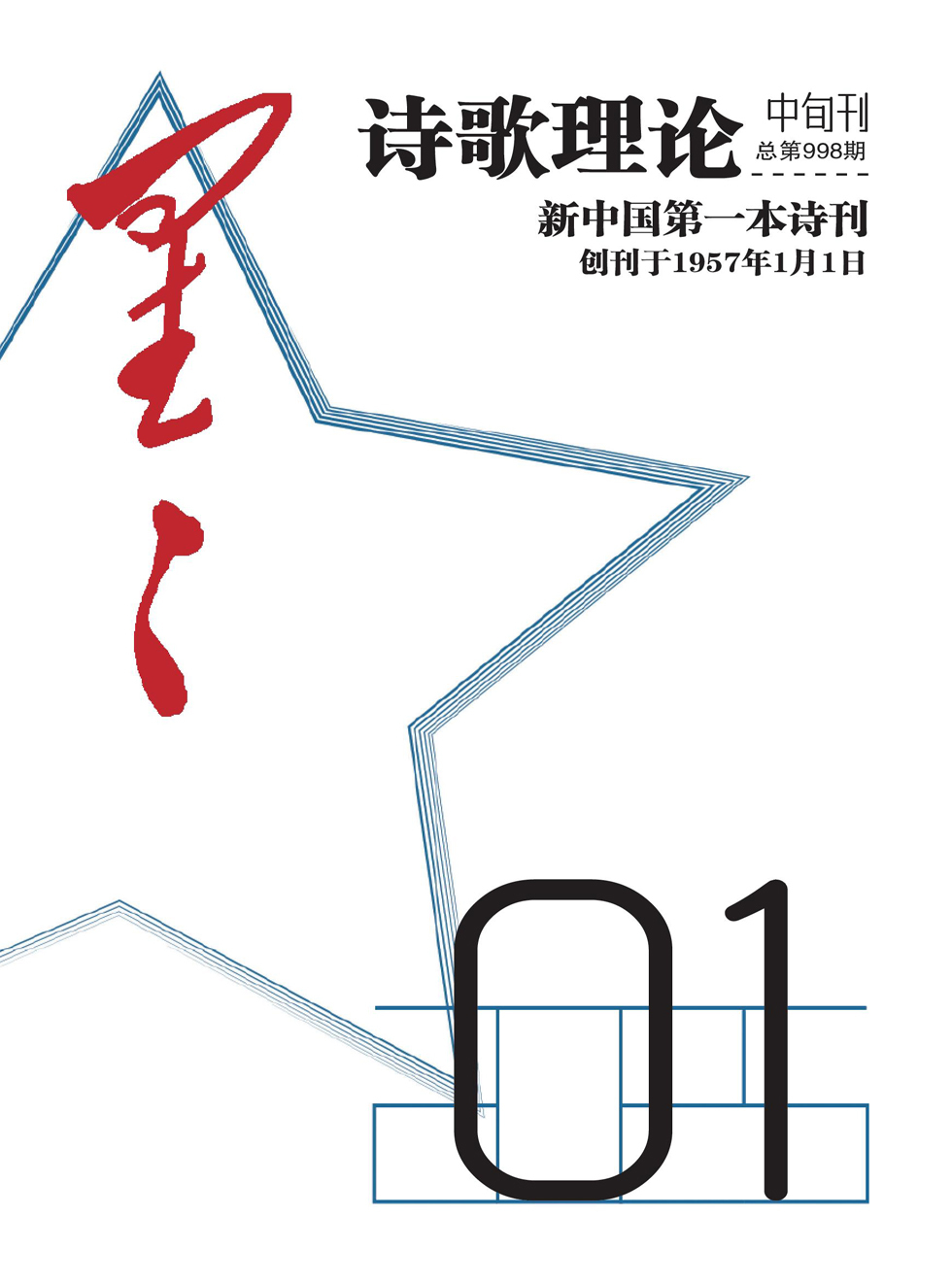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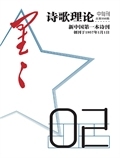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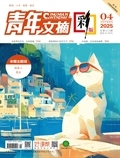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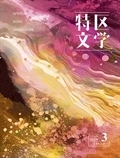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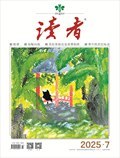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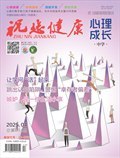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