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分类/
- 文学文摘/
-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
 扫码免费借阅
扫码免费借阅
目录
快速导航-
卷首 | 秋 颂
卷首 | 秋 颂
-

思维 | 守候人生之春
思维 | 守候人生之春
-

思维 | 择书如择偶
思维 | 择书如择偶
-
思维 | 人性的逆转
思维 | 人性的逆转
-
思维 | 最持久的关系
思维 | 最持久的关系
-

视野 | 告别梦境
视野 | 告别梦境
-
视野 | 在河之洲
视野 | 在河之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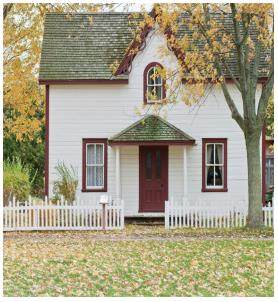
视野 | 住多久才算是家
视野 | 住多久才算是家
-

视野 | 小毕的故事
视野 | 小毕的故事
-

感悟 | 延长中年
感悟 | 延长中年
-

感悟 | 不怕俗,就怕装
感悟 | 不怕俗,就怕装
-

感悟 | 有时家人真可怕
感悟 | 有时家人真可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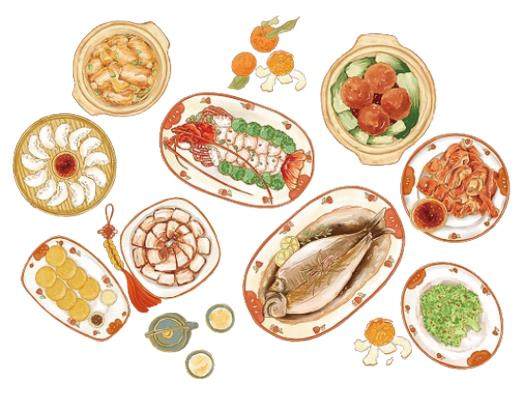
感悟 | 慢慢地学会吃饭
感悟 | 慢慢地学会吃饭
-

感悟 | 第三个人
感悟 | 第三个人
-
感悟 | 专心吃饭
感悟 | 专心吃饭
-
城坊 | 北京和上海
城坊 | 北京和上海
-
城坊 | 一座城,一生缘
城坊 | 一座城,一生缘
-

城坊 | 凉州的方言
城坊 | 凉州的方言
-

城坊 | 一座城,靠什么留住人的身和心
城坊 | 一座城,靠什么留住人的身和心
-
知道 | 为什么距离产生美
知道 | 为什么距离产生美
-

知道 | 《金瓶梅》杂说
知道 | 《金瓶梅》杂说
-

知道 | 学会艺术的生活
知道 | 学会艺术的生活
-

边声 | 烈日·故乡·茶
边声 | 烈日·故乡·茶
-

边声 | 看惯了的风光
边声 | 看惯了的风光
-

边声 | 父亲的“碗”
边声 | 父亲的“碗”
-

边声 | 平常茶 非常道
边声 | 平常茶 非常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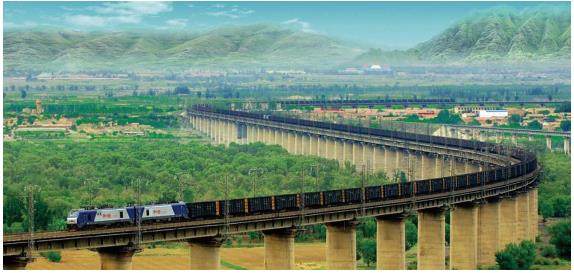
大同大不同 | 山海大秦
大同大不同 | 山海大秦
-

大同大不同 | 四牌楼下的深夜食堂
大同大不同 | 四牌楼下的深夜食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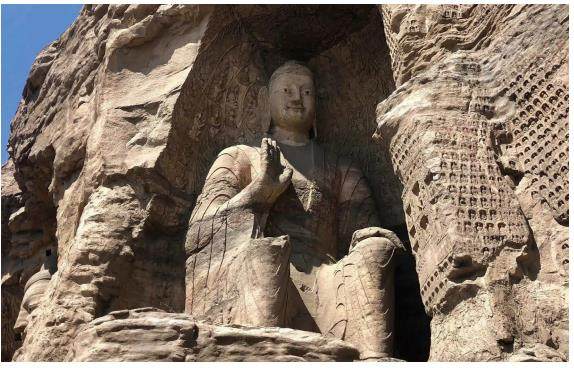
大同大不同 | 击掌大佛与凝眸千年
大同大不同 | 击掌大佛与凝眸千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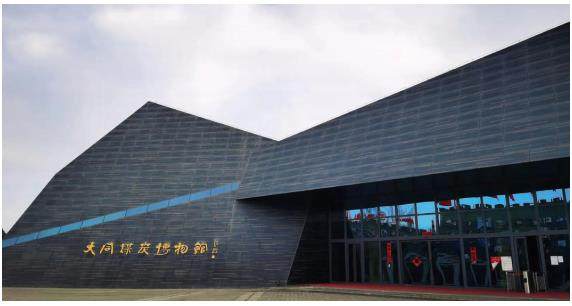
大同大不同 | 穿越古今的煤文化
大同大不同 | 穿越古今的煤文化






















 登录
登录